(美)鲁本. M. 雷尼 撰文 / (USA)Reuben M. Rainey
罗曼 译 / Translated by LUO Man
袁晓梅 校 / Proofread by YUAN Xiao-mei
摘要:阐释了20世纪初曾一度消失的康复花园何以重归美国众多的医疗场所。论述了一个主要由社会学方法提供的事实,即人们接触花园或其他诸如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这类环境对健康十分有益。这种接触能够缓解压力、提高认知能力,并 对可测量的健康指数有正面效应。同时详述了有关花园是怎样改善健康的各种理论。并指出,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尚有分 歧。还通过实例,说明康复花园应由专家团队来设计,根据诸如肿瘤医院、痴呆病院等特定医疗机构的患者与医护人员的 需求量体裁衣。最后提出了一些可能提升康复花园设计能力的研究建议。
关键词:风景园林;康复花园;循证设计;自然;健康;医疗场所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ains why healing gardens are returning to many medical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n absence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discusses the evidence, informed mostly by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at exposure to gardens and other types of spaces such as parks and nature preserves, has positive health benefits. Such exposure can relieve stress, improve cognitive ability, and produce positive measurable health outcomes. The article also recounts various theories of how and why gardens work to improve health, but notes that researchers disagree on this issue. It also makes the case that healing gardens should be designed by teams of specialists to meet the needs of patients and staff in specific medical settings, such as a cancer hospital or a facility for dementia sufferers. It concludes by briefly suggesting a research agenda that sh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design more effective healing garden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aling garden; evidence-based design; nature; health; medical facilities
花园正向美国的高科技医疗场所回归。曾一度被医疗研究人员视作与 医疗保健无关,同时也被医院主管们看作无谓花销的花园,目前正以高科 技医疗场所重要组成部分的形象再现。在美国,这一花园命运的逆转并非 基于某种“新世纪”的迷信,或者凭借直觉的医疗“替代品”,而是基于 严谨的科学调查证据,也即人们常说的“循证设计”[1]。
1984年,美国特拉华大学地理学教授罗杰·乌尔里希发表了一篇有 关医疗环境中“大自然”疗愈能力的研究报告,成为探索更高效人性医疗 空间营造的众多研究者们权威的循证设计模型[2]。许多设计人士都熟悉这 一笼统的研究结论,但细节上仍有待商榷。乌尔里希研究中提出的貌似简 单的问题很快走向了神经系统科学,以及感知、压力和免疫系统间关系这 一富有挑战的研究领域。乌尔里希问道:“患者从病房窗户中看到的风景 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术后康复?”这种研究的变量很难控制,但乌尔里希的 方法就社会学研究的标准来看是精密而完善的。
他调查了宾夕法尼亚州一处有200个病床的城郊医院的46位患者的 住院记录,他们在1972—1981年间进行了胆囊手术。研究对象不包括小 于20岁或大于69岁的、有严重术后并发症以及心理障碍史的患者。病人 被分作2组:一组从病房只能看到一面砖墙,另一组从病房可以看到一片 小树林。分组依据性别、年龄、吸烟与否、肥胖或正常体重、住院经历以及手术年度来平均分配。最终的数据库中详细记录了15对女性患者与8对 男性患者的情况。患者们被随机安置到同楼层一样的病房里,只有窗景各 异。虽然他们的手术医生不同,但均由同样的护理人员看护。
乌尔里希让一位具有丰富外科楼层护理经验的护士详细检查了46名 患者的记录,她并不知晓患者所拥有的窗景体验。这位护士着重3种基本 数据:患者住院期间消耗的强止痛药数量、患者向护士抱怨的次数以及出 院时间。记录明确显示:23位入住小树林窗景病房的患者所消耗的强止 痛药数量较小,抱怨较少,且较入住砖墙窗景病房的23位患者几乎提早1 天出院,其医疗费用也少花500美金。乌尔里希的结论很审慎:“研究结 果表明医院设计应考虑病房的窗景质量。”乌尔里希并非第一个探讨医疗 环境中景观效应的研究者,但他严谨的研究工作是迄今最具说服力的,同 时启发了一大批后续实验,形成了循证设计的指导方针。尤为重要的是, 乌尔里希的实验能显示入住小树林这类“大自然”窗景病房的患者可测量 的正向健康结果。因此,近20年美国新建的许多医院都为病房提供了自 然窗景(图1)。
这项研究大量凭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诸如访谈、问卷调查、随机 取样、统计量分析,以及实地观察等,还算不上所谓的“硬”科学,因为 它无法满足令人信服的重复、变量的严格控制,以及精确量化等严格要求。在医疗环境中开展研究也很困难,各大医院对病人信息都有严格的保密 规定,不同医疗机构的员工、环境及患者也不尽相同,实验操作还可能干扰 医疗过程。尽管存在上述困难,近来的研究还是越来越逼近严谨的硬科学。 通过改进的可视化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跟踪 大脑对环境的动态反应,神经系统科学的这一新发展具备了为更加高效而人 性的医疗场所营造提供设计依据的潜力。另外,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创建虚拟 医疗环境,同时检测它们的心理反应(图2)。或者,人们可以佩戴装有便携式 脑电波扫描仪的帽子,测量大脑对穿越一系列空间时的反应[3-7]。在美国及 海外,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报道了这类风景园林师的工作,他们设计肿瘤医 院、痴呆病院、儿童医院、门诊以及《中国园林》本期主题“康复花园”中 由设计师布莱恩·贝森论述的“俄勒冈烧伤中心花园”。

图1 看到风景的病房,弗罗里达大学尚兹肿瘤医院(弗洛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

图2 研究者在虚拟医院设计中演示多种导示路线(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市)
医疗场所的花园常被冠以“康复”(healing)或“恢复”(restorative) 之名。但是,“康复”概念需要被准确地定义。英语中,heal这个动词意 味着使健全,这种健全包含了心理、生理以及社会多层面。接触花园或其 他形式的大自然可以使体格“康复”,它通过缓解压力给免疫系统带来的 负面影响,与各种药物治疗手段一道促进疾病康复(乌尔里希的景窗研究 就是一个例证)。花园还可以使心理“康复”,它通过使人镇定、保持心 理平衡以及接受现状来达到心理“健全”。在某些条件下,花园可以促进 “康复”,但不能“治疗”。花园无法“治疗”患者的晚期疾病,但人们 可以从接触花园所培育出的心理健全与平静中获益。最后,花园提供了一 个交往空间,患者可以从中获得来自彼此间或亲友们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康复。
这些康复花园到底是怎样对人体健康起作用的呢?神经医学家埃斯 特·斯滕伯格在她最近的专著《康复空间,场所与健康的科学》中就这 个问题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8]。医疗场所花园 的首要功能是缓解患者压力。长期压力对免疫系统带来的高度损伤是毋庸 置疑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以及更多学者的近期研究,诸 如简·克科尔特-格莱泽、罗恩·格莱泽、谢尔顿·科恩,以及布鲁斯·拉宾等人[9-10]。住院治疗带来的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源自体能损失、痛苦的药 物治疗过程,以及恐惧感和不确定性,也同混乱嘈杂、隐私被侵犯,以及 缺乏情感支持的环境有关。抑郁、高血压、强力应激激素的释放也常导致 压力[11-15]。基于这些发现,包括斯蒂芬·克勒特、查尔斯·路易斯、朱蒂 斯·希尔维根、戈登·欧露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玛尼·丹尼尔·温 特伯顿、内奥米·萨克斯在内的一大批研究者,就接触自然对人体身心健 康的积极效应进行跟踪,尤其是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现在,已有充足的证 据表明,长期与植物和非威胁性生物构成的“大自然”接触有利于患者缓 解压力,提升免疫系统的正面效应。可以在病房里培育植物,在芬芳的花 园里漫步,或仅仅透过病房窗户观赏公园般的景致[16-17]。还有研究显示, 除花园外,那些设计良好的建筑要素,如清洁的换气系统、独立病房以及 降噪材料等也能促进患者健康。
然而,为什么接触花园式的大自然会如此有益?研究者们就此有不同 观点。大多数研究者是以类似“生命元素”的方式来定义“大自然”的, 将它理解为存在于他们所研究的空间中的植物和动物。这些空间包括花 园,也包括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大面积区域,由此产生了分歧。有些研究 者认为大自然得以缓解压力的机制根本无法被准确了解,但它的积极效应 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也可以被测量的;另一些学者将其视作一个主要由文 化制约形成的习得反应;还有学者声称这是人类天生的一种遗传素质,被 天地万物强烈吸引并深深依赖,是人类的一种根本属性。这种学派深受生 物学家E. O. 威尔森提出的“亲生命性假说”的影响。威尔森将亲生命性定 义为“关注生命及类似生命形式的倾向”。基于他的理论,这种倾向被编 码进我们的DNA:“……我们的存在依赖于这种倾向,我们的精神也由此 编织而成。[18]”作为人类我们需要接触自然以获得安全感,接触自然是我 们健康幸福的根本。一旦脱离自然,我们就会感到压力。人类之所以被植 物或其他类型生物吸引,是长达200万年的非洲大草原栖息所塑造的人类大 脑和身体的进化结果,正是非洲大草原使古人类得以永续[18]。许多医疗保 健场所的花园设计师们都接受了“亲生命性假说”,以此来说明花园何以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这种论点常被称作是“减压理论”(Stress Reduction Theory),简 称SRT。它的支持者们称有大量的实验证据支撑[13-14,19-20]。然而,这个理论尚存争议,尤 其是人类大草原栖息经历被编码进DNA的说法。反对者们指出这一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 证据,他们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积极反应是一种习得反应,是由文化传播起作用的[21]。
还有其他研究者以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理解大自然的健康效应。这种论点建立在环 境心理学家蕾切尔和史蒂文·卡普兰,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工作之上。这类观点常被称 作“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简称ART[22-24]。依据卡普兰 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大脑会因某种心智活动而感到疲劳或紧张,当接触大自然时 会得到恢复。这种理论较为强调接触大自然是思维能力再生的途径,它关注所要求的任 务,而不只是缓解任务带来的压力。它将大脑看成一种会因某种“直接注意力”的心智 行为而感到疲惫的肌肉。当今的高科技社会频繁地要求使用各种“直接注意力”,例如 操作复杂的机械、撰写技术报告或审计财务报表。这类智力劳动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 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就会产生疲劳和压力,进而导致错误或执行力下降。例如,医生和 护士们时常要做那些集中有意识注意力的工作。当他们长时间工作,就有犯错或判断力 下降的危险。患者和家属们同样会受到影响,尤其当他们想要理解专业的医学术语,以 及复杂的治疗程序时。根据卡普兰和其他研究者的观点,这种智力疲劳以及随之而来的 压力可以被人们所说的“间接注意力”缓解,并达致所谓的“恢复性体验”。“间接注 意力”是不费力和无意识的。它有许多产生方式,但沉浸在诸如公园和花园这类自然环 境中尤为有效。在花园中休闲地漫步,或静坐在花园里,抑或透过窗户观赏风景,都能 缓解由长期注意力集中引发的症状,并恢复其“直接注意力”。这种恢复体验在10~15 分钟就能呈现。基于大量的实验结果,卡普兰及其追随者们断言,花园或其他自然环境 要具备康复效应,必须使人感觉“远离”常规生活,同时令人陶醉,并感受到与整个大 自然融为一体。最终,它应该足够广阔以唤起人们的探索欲望。为了使花园或其他自然 环境产生如此有效的心理感受,必须在设计中展示出“连贯性”“易读性”“复杂性” 以及“神秘性”。“连贯性”使你能够全面了解花园。“复杂性”可增添美学的丰富, 从而避免了枯燥乏味。“易读性”让花园在复杂中更容易识别。最后一点,“神秘感” 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并引你投入其中(图3)[25]。

图3 一个展示了卡普兰及其追随者推荐的“连贯性、易读性、复杂性和神秘性”设计特点的花园(布拉格,捷克共和国)
还有其他理论阐释为什么置身自然能够缓解压力,但“亲生命性”“注意力恢复”以 及“文化价值传播”理论在美国占有主流地位[26-27]。然而“为什么置身自然是有益的?” 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但无论如何,置身大自然都是一剂良药,这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大 量医疗场所的广泛案例研究,伊丽莎白·布劳利、 南希·格拉克-斯普里格斯、山姆·巴 斯·瓦尔纳、小罗杰·乌尔里希、戈登·欧露莎、朱迪思·赫尔瓦根、大卫·温特伯顿及 其他研究者们表明了大自然康复效应是何等的强大且富有革命性[13,28-30]。我们或许不清 楚自然何以如此神奇,但我们能够确凿观察并测量它所带来的积极效益。正如阿司匹林一 样,医生们根本不能完全把握其药理机制,但鉴于它诸多的事实疗效,医生总会用它治疗 病患。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花园,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理论可以阐释花园何以缓解压力与提 升认知能力,但因此将其排斥在医疗场所之外是毫无意义的。
既然康复花园曾经被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它们在美 国的医疗场所里会突然间消失?这段历史冗长而复杂,涉 及医学科学、医疗实践以及空间至上艺术与康复科学间密 切关系,在此仅简述之。
这得从始于18—19世纪初的欧美的阁式医院说起。 这是一种带康复花园的新式医院,其设计是响应这样一种 理论,即疾病都是由“瘴气”,也即腐物所散发的气味, 如尸体、伤口、垃圾和动植物排泄物导致的。由于当时缺 乏细菌致病理论,这类医院因感染致死的病患还很多,但 革新的卫生学实践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为了抵御瘴气的毁 灭性影响,医院要彻底清洁、阳光普照、四面通风且靠近 花园。医生们相信阳光可以净化瘴气,树叶则能滤掉空气 中的瘴气。典型的医院平面由低层楼阁组成,拥有日照充 足的大窗户,以及通风顺畅的长走廊。病房里的床位间隔 很大,同时靠近凸窗。花园要么围合在庭院中,要么以花 床和草坪的形式环绕整个医院。其间点缀着大树,形成校 园般的场所。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就是一位新式医院的倡导者(图4、5)。

图4 一座公园般环境的19世纪校园(夏洛特医院,柏林)

图5 一座19世纪医院的庭院花园(上帝旅馆,巴黎)
19世纪中期,以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为 首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导致了医院设计的深刻变化, 他们创立了细菌致病理论。所有医疗场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微生物感染,现在可以被彻底解决。医生和护士采 用消毒措施,同时医院设计主张使用便于消毒的瓷片或铬 合金材料,越来越多的患者住进隔离病房以防交叉感染。 继德国的医疗实践之后,医学专门化发展迅速,这就意味 着患者要往返于医生办公室之间。在这为高效经济而设计 的,巨大的集中式高层医疗综合体中,患者需要跨越很长 的距离。同时,新兴的医学理论深受实验里的科学家们影 响,而非临床医生。它信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患者 对医疗环境的感知不会影响人类的免疫系统。旧式阁式医 院的花园和庭院被视为与治疗无关,因而成为无谓的昂贵 虚饰。但精神病医院除外,它们继续使用花园作为治疗场 所,或者安置焦躁的患者[31-32](图6)。

图6 一座保存完好的20世纪初为精神病患者建造的花园(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巴尔的摩,马里兰州)
这些新式高层的高科技医疗场所极大地提升了医疗 服务,但这也是有代价的。那些容易清洁的材料放大了 噪声,这是患者压力的主要来源。在不同的专科医生间穿 梭,冗长而无序的走廊增加了患者的焦虑感。和医生的接 触时间总是很短,无法对患者关注的问题深入讨论。“无 菌”之美是病房和候诊区的主要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手 术室仿佛已成为整座医院的样板。简而言之,20世纪的高 科技医疗环境正变得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同样充满压力[9,33]。 不过,对免疫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新研究开启了医疗场 所设计的新纪元,花园与其他减压建筑元素再现,如降噪材料的使用、温馨的色彩配搭、更简单的换气系统、接触自然风景、迷人的雕塑和绘画、明亮的病房、更少的无菌家具,以及供家属过夜的沙发床等。结果是病人的抱怨大大减少,并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新型“功能健全”或“整合医疗”的象征,融合了所谓“以患者为中心设计”的高科技医疗理念[34-35]。
近来几乎所有康复花园都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体,它不仅凭借建筑师或风景园林师的 循证设计数据,还需要医生、工作人员、心理学家和患者合作。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设计挑 战,需要准确理解使用者需求、病情本质、陪护者的忧虑等,同时还要知晓患者需求可能 的变化。一座水花飞溅而有韵律的喷泉能让经历整形外科手术的孩子们开心,但也会导致 成人日托机构里的老人失禁。盲目将花园能带给人快乐这一笼统观念套用到所有医疗场所 是行不通的。
这就意味着康复花园设计必须由团队来完成,并且依据患者及特定的医疗情形来量体裁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康复花园。有专门的痴呆病人花园、儿童花园、癌症患者花 园、烧伤病人花园,以及专属于某个特定医疗 环境的康复花园(图7)。设计团队应由医生、护 士、风景园林师、维护人员、负责预算的医院主管,以及病人和家属组成(图8)。医护人员工作 量大、空余时间少,所以团队协同设计的程序应尽量简洁。特雷西娅·哈森提出了一套高效的团队设计工作程序,只需3次1h的会议[36]。本期主题中由赫伯特·斯卡尔撰写的论文“梅西癌症中心康复花园”中,详细介绍了这套高效工作程序的一个成功案例。

图7 一座具有清晰路径系统的专为痴呆症患者设计的康复花园,生命丰富中心(国王山,北卡罗来纳州)

图8 一座由专家团队设计的康复花园,梅西癌症中心康复花园(里士满,弗吉尼亚州)
专家团队设计固然必要,但对建成后的成果进行评价同样重要。最好在花园建成后几年内进行使用后评价(简称POE)。鉴于医疗环境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很难营造出功能上完全满足患者和医护人员需求的花园。因此观察花园是如何被使用,并对设计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克莱尔·库珀·马库斯指出,使用后评价的形式可以多样化[38]。设计师可以通过访谈了解患者和医护人员对花园的反应,也可以由医护人员进行访谈,还可以请社会科学家团队对花园进行全面评估,但这样花销会较大。
既然我们已知道医院应该带有花园,那么我们能负担得起并良好地维护它吗?面对当今急剧上涨的医疗费用,医院管理者们是否会因面临紧缩医院改造或新建费用危机,从而强制取消花园以及昂贵的“循证设计”元素呢?一项发表在《医疗服务管理前沿》上的近期研究《更好医疗建筑的商业案例》雄辩地指出,这种取消花园建设的策略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文章作者包括2名医院执行总裁,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建筑师。他们指出,包括康复花园在内的更加人性和节能的设计要素虽然昂贵,但一年后就能收回成本,从长远看较那些没有事先整合相关设计内容的医院更加合算,更能使医院繁荣发展[37]。较高的患者满意度、较少的医疗失误、更少的人员流失、较快的病人周转、节省能源,还有其他众多因素可以证明其益处。
在美国,包括圣地亚哥的斯克利普斯纪念医院在内的一些高度精致而成功的医院,其设计已整合了造价不菲的循证设计要素,并带来了经济效益。佛罗里达大学的尚兹肿瘤医院、德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市的圣迈克尔医疗中心、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诊所贡达大楼(图9)都是成功的案例。其中圣迈克尔医疗中心拥有不少于17座花园供人们冥想、游玩、野餐和聚会,成为该医院护理品质和吸引患者的关键要素[9]。

图9 弗罗里达尚兹医学院2014新校园规划中的一个康复花园及公园(盖恩斯维尔,弗洛里达州,弗罗里达尚兹医学院提供)
尽管过去10年间遇到过一些经济问题,但目前美国的医院建设还在增长,其动力源于过度拥挤的急诊室、床位缺乏、人口老龄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新建和改造医院投资的削
减。这为设计更加人性,乃至于其他基于循证设计成果的医疗场所提供了巨大机会,花园也不例外。那些服务于各大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拥有专业技能且富于同情心的员工们永远都是出色医疗品质的最佳保障。然而,这种品质还需要适宜的滋长环境。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营造这样的环境了,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它的品质。康复花园曾一度被视为康复环境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渗透最新康复科学进展的、不断进步的康复空间,花园正重归许多国家的医疗场所(图10)。

图10 弗吉尼亚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儿童康复花园(2014年开放)
然而,还需进行许多研究来使康复花园更高效。有2类特别重要的花园设计领域,分别是外伤后压力失调症患者和受孤独症折磨患者的花园设计。同时需要研究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官在花园疗愈体验中扮演的角色。其他课题包括人们在花园中对颜色的心理反应,以及文化传统和记忆对花园恢复性体验的影响。虽然当前的循证设计文献很多,但许多实验还需要重复以验证其准确性。我听说中国也正在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这些在美国从事康复花园设计研究的学者,非常期盼能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获益,并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
参考文献:
[1] A good discuss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evidence- based design is Cynthia McCullough, ed. Evidence- Based Design for Healthcare Facilities[M]. Indianapolis, Ind.: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2010.
[2] Ulrich R S. View through a Window May Influence Recovery from Surgery[J]. Science, 1984, 224(4): 420-421.
[3] Zeisel J. Inquiry by Design: Environment/Behavior/ Neuroscience in Architecture, Interiors[J]. Landscape and Planning,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4] Edelstein E A. Developing an Evidence Based Design Model That Measure Human Response: A Pilot Study of the Collaborative, Transdisciplinary Model in a Health Care Setting. in AIA College of Fellows 2005 Latrobe Fellowship,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2008: 63-132.
[5] Edelstein E A. Searching for Evidence[J]. Health Environments Research and Design Journal, 2008, 1(4): 40-60.
[6] Aspinall P, Mavros P, Coyne R, Roe J. The Urban Brain: Analysing Outdoor Physical Activity with Mobile EEG[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3: 6.
[7] Deming E M, Swaffield 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quiry, Strategy, Design[M].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2011.
[8] Sternberg E M. Healing Spaces, The Science of Place and Well-Being [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4.
[9] Sternberg. Healing Spaces [M]. Portland, Ore.: Timber Press, 2014: 95-99; 215-252; 227-229; 237; 290-296.
[10] Winterbottom D, Wagenfeld A. Therapeutic Gardens, Design for Healing Spaces[M]. Portland, Ore.: Timber Press, 2014.
[11] Cooper-Marcus C, Barnes M, eds. Healing Gardens : Therapeutic Bene fits and Design Recommendation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9.
[12] Cooper-Marcus C, Sachs N A. Therapeutic Landscape: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Healing Gardens and Restorative Outdoor Spaces[M].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2014.
[13] Gerlach-Spriggs N, Kaufman R E, Warner S B. Restorative Gardens: The Healing Landscape[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5-41.
[14] Heerwagen J H, Orians G H. Humans, Habitats, and Aesthetics[M]//Kellert S R, Wilson E O.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3: 138-172.
[15] Lewis C A. Green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the Meaning of Plants in Our Lives[M]. Chicago, Ill.: Stat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16] Ulrich R S.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Design[J]. Health Environments Research and Design Journal, 2, 2008(3): 61-125.
[17] Rainey R M, Schrader A M. Architecture as Medicine: The UF Health Shands Cancer Hospital, A Case Study[D].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2014.
[18] Wilson E O. Biophilia, The Human Bond with Other Specie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 103-118.
[19] Ulrich R. Biophilia, Biophobia, and Natural Landscapes[ M]//Kellert,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73-137.
[20] Kellert S R. The Biological Basis for Human Values of Nature[M]//Kellert,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42-69.
[21] McKinnon S, Neo-Liberal Genetics: The Myths and Moral Tale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 Chicago, Ill.: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5: 14-71; 120-142.
[22] Kaplan R, Kaplan S, Robert L, Ryan. With People in Mind, Design and Management o f Everyday Nature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23] Kaplan R, Kaplan S.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89.
[24] Gregory N, Bratman J, Hamilton P, et al. The Impacts of Nature Experience on Huma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ntal Health[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18-136.
[25] Kaplan, Ryan. With People in Mind[M]. 7-16.
[26] Appleton J.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rev. ed[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6.
[27] Bratman, Hamilton, Daily. The Impacts of Nature Experience on Huma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ntal Health[M]. 124-131.
[28] Brawley E C. Design Innovations for Aging and Alzheimer’s[M].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2006: 275-295.
[29] Ulrich R S. Effects of Gardens on Health Outcomes: Theory and Research[M]//Cooper-Marcus and Barnes, eds., Healing Gardens, 27-86.
[30] Kellert,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M].
[31] Two excellent historical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of healing gardens in Europ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Edwin Heathcote, “Architecture and Health”[M]//Jencks C, Edwin. Heathcote, Maggie’s Cancer Caring Centers, London: Francis Lincoln, Ltd., 2010: 54-91.
[32] Warner S B, Jr. The History[M]//Gerlach-Spriggs et al., Restorative Gardens, 7-35.
[33] Warner. The History[M]. 21-24; 31-33.
[34] Jencks, Heathcote. Maggie’s Cancer Caring Centers, 81-91;
[35] Verderber S, Da vid J. Fine, Hea lthcare Architecture in an Era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3- 329.
[36] Cooper-Marcus, Sachs.Therapeutic Landscape[M]. 47-55; 308-315.
[37] Berry L L D, Parker R C, Coile D K, Hamilton D, et al. The Business Case for Better Buildings[J]. Healthcare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4, 58(11): 76-78; 80; 82-84.
作者简介:
(美)鲁本. M. 雷尼(Reuben M. Rainey)/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建筑系荣休教授/弗吉尼亚大 学建筑学院“设计与健康中心”联席主任
译者简介:
罗曼/1989年生/女/河南信阳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641)
校者简介:
袁晓梅/1968年生/女/工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广州市风景园林重点实验 室成员/本刊编委(广州 510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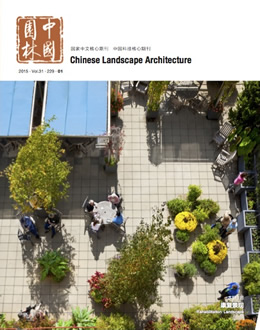 《中国园林》2015第1期导读
《中国园林》2015第1期导读
Leave a Reply